 【資料圖】
【資料圖】
□張艷霜(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研究生導師)
《聊齋志異》中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姓許的捕魚人每晚喝酒時都會斟一杯酒祭奠水中的溺亡人,如此感動了一個因醉酒溺亡的水鬼王六郎。他以驅趕魚來報答,讓許漁翁每次都能滿載而歸。兩人見面后結為莫逆之交,成為知己。王六郎大限將至,須索一人命替換自己方能投生,但他卻因不忍心殘害人命而放棄投生機會。王六郎的善心感動了玉帝,讓他變成了保護一方民眾平安的土地神。后來許漁翁不辭辛苦前去看望,王六郎通過各種方式真情款待。這個故事展現了人鬼之間、人神之間的真摯情誼,人鬼之間也可以成為知己;置身青云,無忘貧賤,所以才成為神。
形體面具戲《水生》的故事原型就來源于蒲松齡寫的這個神鬼故事,講述了一個尋找替死鬼的水鬼與一個心地善良的漁夫之間關于友情和人性的故事。形體戲劇作為戲劇的一種新模式,最早出現在上個世紀50年代的歐洲,本世紀初才進入中國。法國著名導演、戲劇理論家雅克·勒考克是形體戲劇發展最重要的推動者,也是使形體戲劇從啞劇中脫穎而出的奠基者。形體戲劇的核心理念是:身體蘊含著符號美學,身體成了戲劇的中心。而三拓旗劇團作為國內形體戲劇的代表劇團,通過以《水生》為代表的一系列形體戲劇,不斷追求“哀傷的幽默”和“精彩的想象”的演劇風格,探索著“詩意的身體”的表現智慧。
《水生》的故事是簡單的,但表演是極其獨特的。在桂林山水實景中搭建的一個簡單舞臺,構成了或許是國內最貼合本劇內容的一版戲劇空間。四盞燈籠是整出劇最重要也是最靈活的道具,它們不僅僅標注了橋和河的界限,也分別用黃色、藍色、紅色代表了陸地、河流以及惡魔登場后的恐怖氛圍。此外,真絲舞扇的使用代表了水中游動的魚,配合表演者的肢體動作,虛擬出漁夫滿載而歸的場景,構思可謂是頗為巧妙、頗具想象力。從布景、燈光、道具到表演者,一個假定的戲劇空間便形成了。
《水生》的一個重要特色是添加了儺戲的表演形式。儺戲,又稱鬼戲,是我國最古老的一種祭神跳鬼、驅除瘟疫、表達安慶的娛神舞蹈。表演時借助木雕或獸皮面具來塑造人物。而根據勒考克的“中性狀態”概念,形體戲劇演員戴上“中性面具”,處于一種探索、開放、注意、聆聽并真實感受事物的狀態。《水生》貫徹了這一理念,主要演員都頭戴黑紗、佩戴面具并身著“中性服飾”,隱去演員本身的面目,讓身體在表演中更加凸顯,肢體動作的作用被擴大到承擔演員的臺詞、表情、動作乃至傳遞情緒的任務。身體外化了人物的內心,配合觀眾的想象力,一起完成創作者設定的敘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幕是,水鬼在第二次與惡魔斗爭時,兩只眼睛被魔鬼挖出。表演者的面具此時垂出紅色的布條以代表血淚,加上表演者雙手抓地、掩面搖頭、爬行翻滾等形體動作,將水鬼失去雙眼后的痛苦表現得異常生動。此時無聲勝有聲,水鬼無聲的痛苦吶喊已在觀眾心中響起,并激起一陣陣憐憫。
《水生》中的音樂也極具特色,雜糅了蘇州評彈、西洋樂、笛聲、鋼琴等東西方元素,形成一種奇妙的融合。其中的蘇州評彈唱的是清代彈詞《珍珠塔》的故事:相國之孫方卿,因家道中落,去襄陽向姑母借貸,反受奚落。表姐陳翠娥贈傳世之寶珍珠塔,助他讀書。后方卿果中狀元,告假完婚,先扮道士,唱道情羞諷其姑,再與翠娥結親。雖然這則民間故事與劇的內容無關,但借漁夫之口唱出,卻非常符合其身份與風格,也為本劇更增一份中國傳統戲曲文化的底蘊。
與西方的純愛與浪漫元素相比,中國古代的人鬼故事總是多了幾分豪俠氣息,導人向善。《水生》中水鬼的善,讓他無法找到替死鬼;而漁夫的善,讓他愿為知己獻身,助其解脫。作為首個在愛丁堡藝穗節獲得獎項的中國劇目,《水生》將中國傳統故事與東方美學做到了完美融合。三百年前的一個鬼故事結合遠古時代的巫術形式,在表演者的形體演繹下,超越了語言、超越了時空,激蕩起所有人類的思考。水中的世界映射著真實的人類社會,煉獄有愛,邪中有善,而善才能成就最美的傳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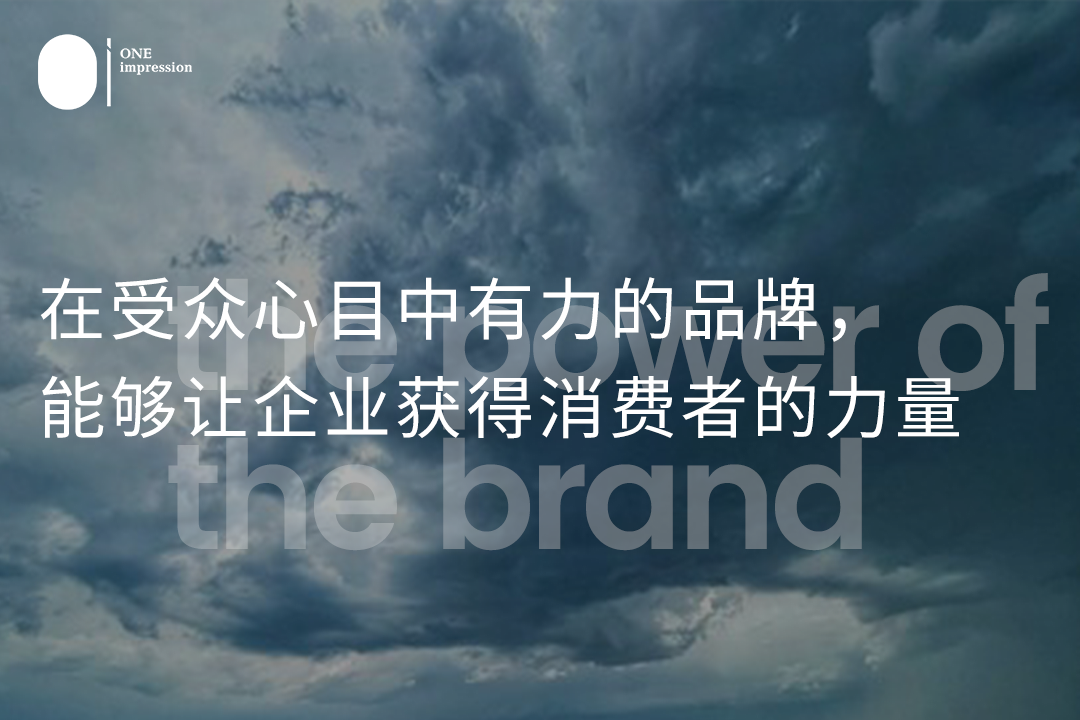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